冰心散文奖获奖书籍是什么(冰心散文奖得主刘诗伟谈人间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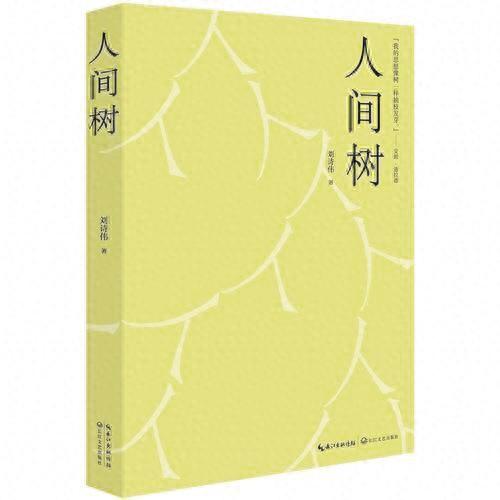
湖北作家刘诗伟近日接连斩获重要文学奖项,一是散文集《人间树》获冰心散文奖,一是长篇小说《一生彩排》入围2023“新芒文学计划”。
《人间树》是刘诗伟的最新作品,故乡的人、故乡的事,小小的兜斗湾是至真的人间,在刘诗伟如诗的叙述中,故乡所有的悲喜如在眼前。诗人、评论家徐鲁撰文说:“刘诗伟是文学界公认的一位优秀的小说作家。读了他的散文集新作《人间树》之后,我禁不住要感叹:他的散文才华被他的小说给遮蔽了!”
《人间树》全书收入15篇长散文,分为“乡亲们”“上辈人”和“我自己”三辑。从故乡走出去的游子,读这部散文集一定会感觉到亲切。1月11日,刘诗伟接受了极目新闻记者采访谈创作感受。

作家刘诗伟喜获冰心散文奖
“在对故乡的整体感知中,我发现和提炼了人与树的关系意象”
极目新闻:俗话说,近乡情怯,越是身边的亲人,越是家乡人,越是不好写,怕写不真,又怕写得太真。您是用什么标准选择和书写人物的?比如村里的那几个人物?
刘诗伟:这是一个具体而尖锐的问题,事关文本的品质与价值。亲人和熟人之所以不好写,大概因为写得“不真”就破产了,写得“太真”往往立不起来;又或许有“对号”不符或令人不悦的顾虑。我的方法是跳过这些,只管找到“生活的艺术”。布莱希特说:一切艺术都是为反映最大的艺术——生活的艺术。在对故乡的整体感知中,我发现和提炼了人与树的关系意象,那些“人与树”的故事是特定时代与自然里的生命样态与生活写照,它们的质感是日影、树阴、汗珠、稻穗、桃花、蝉鸣、落叶以及童年的赤脚与祖母眼中的盼望,无比具有万物原生的质素,映现广义自然的辉光——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它们同情、同理,对它们深怀敬意。一直以来,那些为了生命的生活与为了生活的生命的殷殷状况令我怜爱心动,那种包含社会的广义自然与包罗万物的客观生态的本义让我明澄坚定。——有了这个,我便感到接近了“生活的艺术”,便有了对人与事的取舍尺度;或者,其实就基于对故乡整体生活的深度感知,去发现、选择、开掘人物与故事的相对统一的最大意义。此间,真诚与符合真理的善意是写作的最大方法,也是写作的最大保障。
没有新意的写作是无效的
极目新闻:您写父母,对父母的感受,为何与兄弟姐妹的感受不同?从真实的生活素材到文学文本应该怎么淬炼?在这一点上,对想要学习写作者,有什么建议?
刘诗伟: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没有新意的写作是无效的。父母与兄弟姐妹通常是最熟悉的人,怎么写他们呢?实际分两类情况:一类是初学写作者,比如中小学学生,能写出家人的个性与特征就好了,因为这类写作不是拿出去发表的,是练笔;另一类是力图发表传播个人作品的写作者,如果单是像学生作文那样写出个性与特征是不够的,还得以既有的全部的同题材的作品为对照系统,检视个人作品是否有新意以及新意的价值如何——没有新意或新意薄弱,就不要写、不要谋求发表(只为自娱自乐也不错),这是作家或创作的伦理;不过,作为人物的父母与兄弟姐妹总归是各有特点的(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绿叶),关键在于发现与开掘。此外,有了独特的人物与故事,怎么写是必须讲究的,视角、结构、节奏、语法、风格特别重要,也应当有特点或新意——这个需要大量阅读与操练。
故乡人与事物、生活与期冀,注定了我的人格逻辑
极目新闻:《人间树》获得冰心散文奖,您有什么获奖感言?从情感上讲,这部书对您意味着什么?
刘诗伟:我的童年在江汉平原的光景里。放学时,我走在河堤的树下,看见田野远处散落一些黑点儿,知道有一粒黑点是我母亲。树是平原的福祉。天热,母亲去田头的河渠捧水喝,顺便在渠岸的树下躲一会儿阴。她晓得那个湾子的每一棵树,包括样子与结疤……她和它们同在风雨冷热中,每天每时,就是在一起。因为童年,因为遐想与关切,我了解那个湾子与树的故事。那个湾子与树同是自然,同是生态,是世间原生的叙述——因为原生,格外沉稳正大。
我写这本书,主要基于珍惜与热爱,对生命的珍惜,对生活的热爱;故乡的人与事物是我童年与少年时真切感受过的,那种清贫生活中的生命状态是生动的,那些平凡生命的生活期冀是深刻的——它们注定了我的人格逻辑;然后,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我一直关切社会生活,包括故乡的生活,当我以较为宽阔的视野观照社会生活并以故乡生活为视点加以考察时,我的思绪复又漫延到人类生活与广义自然的视域,我的认知驱使我用这个时代最文明的生态观或自然观去擦亮我所珍惜的生命与热爱的生活。情感需要理性帮扶,抵近真理的情感才是文明的深沉的情感。
真正的作家捍卫的是文学性,而不是写法与文体
极目新闻:《人间树》是散文,也很有故事性,很多地方有文外的意味,有借鉴小说的手法吗?您怎么看当今散文文体的创新?这样一种写法貌似近年比较受欢迎。
刘诗伟:问题涉及多个层面,我混合回答。往大里说,一切的“文”都是因应现实生活、因应审美诉求、因应文字载体(包括书写方式与传播方式)、因应传播接受语境的演进而演进的结果,这是中外文学流变的事实;文学创作的任何嬗变(包括文体与写法的嬗变)都可以从中找到确凿的理据。但有限的文学教育带来的习惯认知为之诧异并与之抵牾。基于此,您所说的“貌似”乃为“其实”。在越来越开放的传播语境里,文学不变的结果是产品过剩、是穷途末路。当然,由于读者众多而且文学认知参差、文学阅读量不同,“不变”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内是存在实际消费的。致命的前提是文学性。雅各布森说:文学性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那个东西。简言之,“那个东西”就是作品能让读者感受审美愉悦的东西。“文”或文学的写法与文体不断演进变化,而文学性是恒稳的品性。所以,真正的作家捍卫的是文学性而不是写法与文体。
我的散文有小说的手法,评论家做过学理分析。对于我,这是自然的:一是我主要写小说,手法比较熟,包括发挥故事与白描的艺术功效;二是文体自觉——我了解散文的许多款式,看得出它们的技术优劣;三是寻求符合生活的表达。比如语言吧,像我这个岁数的作者,在新时期初的教育背景下学文学,从古典与传统那里学过来,曾经做过文言文写作训练,但文学性指引我投奔“生活的艺术”,生怕在那些旧词章里逃不出来,我必须尝试在鲜活的生活语境中再造语法(广义的语法)——这是大事。




